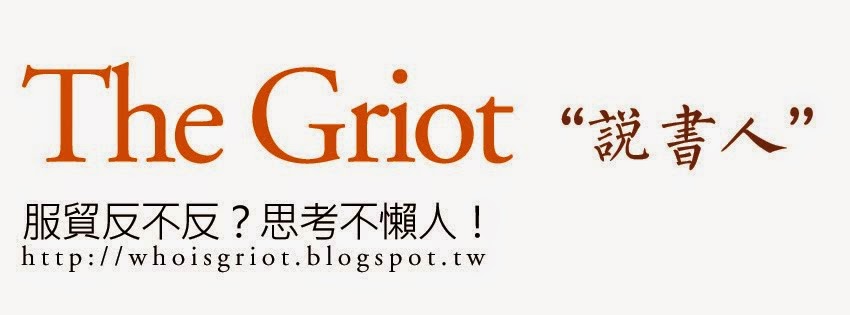近日在反服貿學潮中,看到楊逵的外曾孫魏揚也牽涉到進佔行政院的事件,感慨萬千,不禁想起四十多年前與楊逵先生的一段歷史因緣。
民國六十一年夏天,在保釣運動所帶動的台灣學生對兩岸歷史的重新認識的動力與氣氛下,我們有一個機會來到台中大度山上的東海大學,透過老友的介紹認識了在大學附近開墾一片花圃的楊逵先生,重新串起台灣戰後新生代與抗日前輩的歷史連結。
這是我十三年前在拙作《青春之歌》裡的描述:
在這種求變的氣氛中,林載爵也困頓地摸索著求學的方向,與在台北的我們一樣處於釣運之後的變局之中,一九六○年代的台灣啟蒙前輩並未能提供令他滿意的答案。這時他在東海校園周遭一貫的上下求索中,一個偶然的機緣走進了學校對面的東海花園,去認識了花園主人楊逵,並因而開啟了我們重新認識台灣左派歷史之門。……
……民國六十一年間,正當我們在台北摸索著左翼的另類方向之際,再一次來到東海。載爵這次又興奮地向我們說起另一個大發現,這次他發現的就是台灣的左派前輩楊逵,以及他所寫的一部描寫台灣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小說《送報伕》。他興奮地拿出手抄的《送報伕》來給我們看,當我們讀到這篇日據時期所寫的小說結尾:『我滿懷信心,從巨船蓬萊丸的甲板上凝視著日本帝國主義佔據下的臺灣的春日,那兒表面上雖然美麗肥沃,但只要插進一針,就會看見惡臭逼人的血膿的迸出。』這段話真是令人熱血沸騰。我們又得知將日文原著翻譯成中文的竟是三十、四十年代大名鼎鼎的胡風,心裡更是有數了。於是載爵又帶領我們越過馬路到東海花園去拜訪小說的作者。
楊逵這時住在花圃中的一個簡單農舍,讀小學的孫女楊翠陪伴著他,還有一位與他一起坐牢的農民同志在花園幫忙。他對我們這些後生晚輩的來訪很感欣慰,每次總以台灣傳統的米奶款待。他已安於歸隱的園圃生活,對過去的歷史並不多談。然而我們還是從他這裡觸摸到一些日據時期的農民運動與工人運動的風貌,而能將台灣放回第三世界的格局之中。
這可是我們一年來的另類摸索可以具體接得上的歷史線索,而且是由楊逵這一位有血有肉的歷史參與者來向我們呈現的。然後當得知他曾將大兒子取名為楊資崩,以期待資本主義體制的崩潰時,我們這些後進對於台灣左派前輩信念之強烈與情感之浪漫,更是感到萬分地震撼與折服。
為了追尋前輩的足跡,載爵開始探討台灣歷史與文學,並挖掘楊逵的這段歷史。他先為《東風》寫了一篇〈訪問楊逵先生──東海花園的主人〉,不獲校方准許刊登,於是又再發心撰成〈台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鍾理和之比較〉一文,登上了台大外文系顏元叔教授主編的《中外文學》,楊逵遂再度為台灣的知識界所知。楊逵被載爵挖掘出來之後,重新與當時台灣的文化知識圈掛了鉤,他所代表的的歷史意義遂重被肯定。我們高中時代的朋友林瑞明還因此機緣,後來以林梵為筆名寫了《楊逵畫像》一書。
不管如何,在左翼傳承幾乎完全斷裂的這時,楊逵的重現代表著與此傳承重新接軌的一絲希望。在這之前,我們曾透過[各種可能取得的書刊來重新認識台灣日據時代抗日歷史與前輩],但是畢竟需要真實人物如楊逵者的現身,才能讓我們真正觸摸到台灣過去的左派傳承,才讓這個斷裂後的藕斷絲連有了重新接合的可能。
此後我在畢業、當兵,而於民國六十四年出國之前,就屢屢來到東海花園拜訪楊逵老先生,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在台中成功嶺接受預官訓練時,曾在寫給友人的信上如此提到:
昨天中午從營裡放假出來,我直奔大度山上載爵處,待了一下就同他到東海花園去了。他是去做工的,我也跟著換了雙破鞋,捲起衣袖褲腳,跟他挑水挖土澆花。搞了一兩個鐘頭卻一點也不累,對自己的體力甚感滿意。我們一直待在那裡吃了晚飯,飯後大家喝紅標米酒,抽長壽煙,啃著花生米。楊老先生酒酣耳熱之餘,暢快談起當年往事。我們聽著他用那蒼勁的聲音,東碰西撞地講起似乎已屬上個世紀的英雄故事,隨時又穿插著他小孫女清脆的笑聲,對照起我那軍隊的受訓生活,真有如置身世外桃源!
楊逵的抗日意識乃是基於弱小的殖民地人民反抗日本帝國壓迫的動力,而當年這一種反抗的資源主要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左翼思想與第三世界意識。這個反抗所反對的不僅是日本帝國主義而已,更是其所從出的歐美現代帝國對全世界弱小民族所進行的領土侵略、經濟剝削與文化摧殘,這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追求國家自主發展與互相平等對待的第三世界意識。可以說楊逵及其抗日同志當年的壯舉,是有著這麼一個全球性的反帝運動的左翼連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