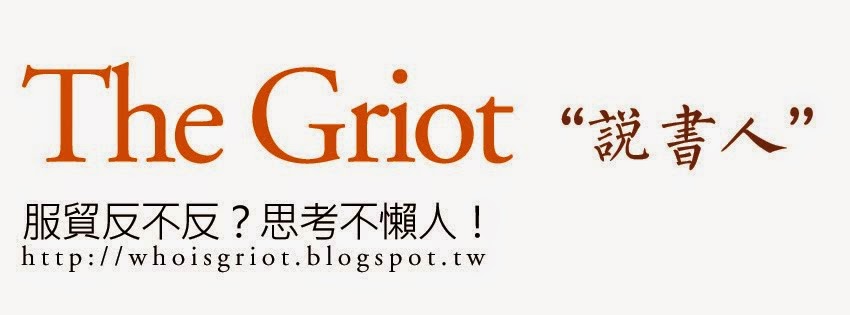|
| (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提供,伍逸豪攝) |
前幾天在《自由時報》上看到龍應台部長批評太陽花學運,說它「思想非常薄弱……充滿矛盾跟沒有想透的東西」,好比說,學生宣稱捍衛民主卻破壞法治,嘴上說堅持程序正義,但卻又以行動顛覆了他們自己的堅持。這個批評立即招來了運動指揮者及多名綠委的反擊,異口同聲指責龍女士昨是今非,且謂真正思想薄弱的恰恰是龍女士自己。[1]
《自由時報》把這個消息置於頭版,並且搭配了一張網路上署名「熱血時報」對照今昔的諷刺圖文,意欲對比出昔者龍女士野火燎原何其粲然,今日龍女士墮落反動一至於斯。「熱血」對此「墮落」的「解釋」是八個大字:「通匪令人神經失常。」[2]
記得看了這篇報導,當時的立即反應只能說是「啞然失笑」。龍女士是否真的「神經失常」,不是「熱血時報」說了算,若依我「個人看法」,應該是沒有的,我有過好多論敵,其中包括龍女士,但我從不認為對方是「神經失常」,但當然我說了也不算,按照此間流行的說法──這種問題必須經過「專家確診」。
但若是懸置確診,只就「通匪」這一「病因」而言,以我對作家龍女士的理解,我願意挺身而出,作如下之證詞:龍女士是台灣這十餘年來在文化戰線上克紹冷戰遺業反共不懈的先鋒戰士。長期以來,她以「民主」、「自由」、「多元」的台灣文明論,批判「專制」、「落後」、「野蠻」的現當代中國及其共產革命。在入閣當官之前,她以此為志業密集著書立說,曾發表了喧騰一時的著名批判中共與當代中國的文章〈請用文明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而前幾年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更是她在這方面的持續戰鬥的攀顛之作。說龍女士「通匪」,反映的是當今學運以及其後的這整個時代精神狀態的一個核心病象:為了我們的「正義」,我們可以完全粗暴地對待歷史。「未來」,於是僅僅是吾人的意志對象。出現了這樣的一種「去歷史觀」,難道不該刺戟吾人嚴肅思想嗎?
作為龍女士的一個長期批評者,由我來為她洗刷「罪名」實感荒謬、無奈,甚至悲涼。然而,我並非徒為龍女士悲,所加於彼之罪固然無稽,但奈何其半自取。聽清楚,我是為當前學運的一種幾乎可說是界定性的狀態而痛心:凡是批評這個運動的,就必然是心神喪失的不正常之人。若問何令致之?答曰,一切唯因「通匪」,而匪即是馬即是中,三位一體。於是,整個島嶼就只存在兩種人了:那光明的道德的不通匪的,與那黑闇的邪惡的通匪的。後者合當引入歷史灰燼之中,不只是因為「通匪」,還更因為他們只有百分之九。這裡有一種流行已久但再攀新高的族類主義、排他主義,以及眾暴寡主義。從這個視角看,於是「反服貿」其實不過是另一個驗證敵我的准軍事口令而已,連我們很多「左翼的」、「批判的」朋友如今也接受了這樣的口令,以之質疑昔日戰友,遑論其餘。「通匪」這個冷戰話語竟然能夠在解嚴與全球冷戰結束近三十年之後,再度成為此間學運的一個日常語詞。光是這一弔詭事實,難道不就該刺戟人們嚴肅思想嗎?在沸騰的熱血中,是否蓄積了大量不為我們所意識得到的冷戰殘餘。
但是當一切複雜的現實與爭議都可以如此義無反顧地簡單一刀切時,歷史和思想又如何能找到它們在運動中的位置呢?學運從來沒有比此時更需要自我批評與外部批評。但是學運在面對它的批評的當兒,卻又只能自我演出它所極力否認的那個病徵──血氣亢奮,思想薄弱。幾乎沒有看到學運領導本身或是支持學運的「學界」對兩個淺而易見的現實問題,提供過他們的反思。這兩個問題是:一、此刻正在島嶼上酲醉狂飆的這樣的一種族類主義與排他主義,是之前的藍綠撕裂的救贖呢,還是變本加厲?二,如果這樣的一種極端善惡二分的「正義感」,再在將來添加上權力之翼的話,那麼是否宣告了一個結合內在恐慌與體制暴力的新白色恐怖時期的降臨呢?古人說,居安思危,那如果居不安尚不思危呢?